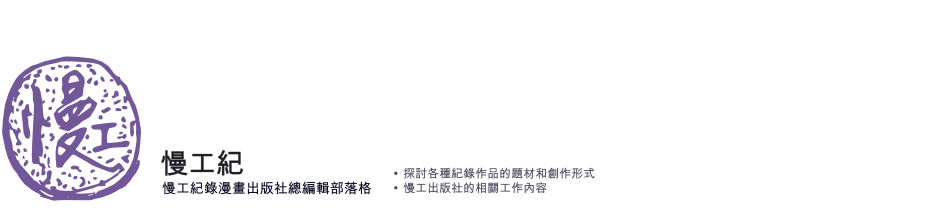|
| Harvey Pekar from http://thebluegrassspecial.com/ |
 |
| Harvey Pekar & Rober Crumb |
Pekar的最後一個遺作是
HarveyPekar's Cleveland,這篇是在他過世前就完成文字了,並在他過世後由新生代的畫家Joseph
Remnant完成,於2012年出版為一本120頁的單行本。
本書講的基本上就是Pekar本身在Cleveland從出生到退休的故事
-
可以說是從個人的層面紀述了Cleveland市及他所長大的猶太人區興衰的歷史,頗有Will
Eisner紐約三部曲的感覺。在這個故事的第一頁,
第一句文字(而且第一頁就這一句而已),寫的正是,"Yeah,
I've had plenty of good day..."
(我這輩子算過得不錯了…)。簡直是在預告這將會是他最後遺作…。
美式主流漫畫界的名作者 - Alan Moore(英國人)只寫不畫,他的作品包括 V for Vendetta 和 Watchman等等,可以說是超級英雄裡較不那麼super、比較dark、比較punk的東西。這位主流的大腳給Pekar寫的遺作寫了序:"Yeah I've had plenty of good days." Thus commences one of the very last and one of the very greatest works by that unique and irreplaceable American voice, the truly splendorous Harvey Pekar. 這個推崇也許證明了Pekar在漫畫界中比他書中的那位平凡小人物,更重要更具影響力。
美式主流漫畫界的名作者 - Alan Moore(英國人)只寫不畫,他的作品包括 V for Vendetta 和 Watchman等等,可以說是超級英雄裡較不那麼super、比較dark、比較punk的東西。這位主流的大腳給Pekar寫的遺作寫了序:"Yeah I've had plenty of good days." Thus commences one of the very last and one of the very greatest works by that unique and irreplaceable American voice, the truly splendorous Harvey Pekar. 這個推崇也許證明了Pekar在漫畫界中比他書中的那位平凡小人物,更重要更具影響力。
對Pekar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網站:PekarProject
以上感謝JiMMy所提供的資訊。
以下為作者陳蘊柔於TaiwanComix 4中所發表的文章:
從不別過頭去的Harvey Pekar
“ A brand new decade, same old bullshit” 這句話自2008年一直掛在我msn暱稱上,出自哈維.皮克Harvey Pekar的傳記電影《小人物狂想曲》(American Splendor, 2003),當時只是覺得這句話很酷炫,有著特殊的文字節奏,但其實這句話不僅道出了藝術家創作的瓶頸,無法突破總是原地轉圈的困境;也說出了很多人日復一日不知所做為何的庸碌生活。而我在不自覺的情況下因為這部電影,或者說因為哈維.皮克這個不平凡的小人物,開啟了之後對歐美漫畫以及地下漫畫的熱愛。
Harvey pekar 的傳記電影《小人物狂想曲》(American Splendor, 2003) 預告片:
哈維.皮克1939年生於美國克里夫蘭(Cleveland),一個治安欠佳、充滿抑鬱氣息的工業城市,直到退休他都是在醫院當檔案管理員,每天為金錢、婚姻種種問題困擾著。這樣的人跟你我沒甚麼不同,每天都有瑣事煩心,人生只能用混亂來形容。他生活的樂趣大概來自於收藏爵士樂唱片以及閱讀,直到30幾歲透過收集唱片的同好,認識美國地下漫畫家Robert
Crumb。在滿足自己收集唱片與文學閱讀的興趣之時,哈維也意識到自己的創作慾望及不平凡的美學敏感度,進而開始創作漫畫,於是與Robert
Crumb合作自行出版了AmericanSplendor,記錄自己的日常生活。
哈維的漫畫創作與一般的漫畫家不一樣,他擅長文字,但對於繪畫一竅不通,他發展出自己的漫畫創作過程,只畫出火柴人、做漫畫框的安排、寫出對話與方框文字,將草稿交給合作的藝術家,討論背景與人物的設定,然後由藝術家產出漫畫。這大大的開啟了漫畫更多創作的可能,對於哈維來說,漫畫是有無限潛力的一種載體,交由不同的藝術家詮釋他的文字,改變了大家對於漫畫中圖文關係的偏見,漫畫的圖文關係不是只有圖引導文的可能,雖說許多強調動作性或氣氛的漫畫中圖像的支配的確強過文字,但仍有一種可能是圖像與文字相輔相成、互相補充、互相搭配,哈維的作品就是很好的例子:思辯的過程、內心獨白透過文字呈現,而畫面氣氛的掌握、人物形象情緒則靠圖像展現。
 |
| Harvey Pekar & Joseph Remnant |
 |
| Harvey Pekar & Rober Crumb |
 |
| Harvey Pekar & Josh Neufeld |
哈維作品其中常被提及的另一項特點在於,他作品的寫實性以及自傳性。自傳性漫畫或自傳圖像小說的成功,從60年代地下漫畫Robert
Crumb、Harvey
Pekar之後Art
Spiegelman的Maus到現在的自傳漫畫:艾莉森.貝克德爾的《歡樂之家》(The
Fun Home),
瑪嘉莎塔碧的《我在伊朗長大》(Persepolis),以成人為導向的漫畫中,自傳漫畫的發展可見一般。與其他自傳漫畫作品不同的是,哈維所呈現的自傳內容是取自平凡日子中遇到的瑣事,不像Art
Spiegelman的圖像小說,講述納粹倖存者的父親的往事以及父與子間衝突;歡樂之家圍繞的是作者與父親特殊的關係、同性戀的自我認同與覺醒,這些作品所描述的都是特別的事件、改變他們一生的關鍵。
而哈維卻是紀錄、呈現日常生活,但由於他絕佳的觀察力與描述能力,旁人的對話、討論書籍、音樂、他的檔案管理員工作、甚至拍自傳電影以及得了癌症的治癒過程都成為他的題材,小到洗碗總是洗不乾淨、與鄰居的對話、大到面對癌症的過程,哈維可說是近乎赤裸的將自己的人生寫進他的漫畫裡,許多尷尬、醜陋的事情都盡可能誠實得呈現。
 |
| Harvey Pekar & Joseph Remnant |
他曾說過,覺得自己會選擇寫自傳性的作品可能是因為他比別人更自我,而且光是了解自己以及周圍所發生的事情就已經夠忙、分析不完的。哈維不推崇美化過、超乎現實的故事和幻想,他知道有許多人無法看他的作品,因為讀者不願回家還要被迫面對、被點醒他們所處的困境。但哈維的創作信念卻是,不走利用文藝逃避現實那套,要讓讀者面對生活的煩惱,但用一種「哈維式」的幽默但誠實的眼光去看待這些問題,每棟公寓的一扇窗裡,都可能有人跟你有著同樣的處境或是痛苦的當下,你也可能看到漫畫中人物的痛苦因而慶幸自己生活不算太糟。
他觀察自己的生活也傾聽別人的故事,利用大量細節的供應、俗語、俚語以及方言來讓讀者更信服他的故事,但他在訪談中提醒讀者,意識到故事被記錄下來的虛構性,American
Splendor中的事件時間可能會被濃縮,人物許多會被他換名字或是性別。有時因為長期細密的紀錄生活事件,導致漫畫影響他的行為,與別人交談時可能使用各種別種語氣和問法來引誘別人講出適合寫進漫畫的題材,這樣的細節他都坦白不諱,看得出哈維對自己作品寫實性的要求程度;他誠實描寫自己的焦慮、性格上的缺陷,他與周圍的人相處的情形(有些非常尷尬),如同其他自傳小說或自傳漫畫,作者的生命與讀者貼近的程度超越其他文類,我想這也是哈維作品或是自傳漫畫吸引我的原因之一。
0:45出現的便是Harvey Pekar :
"On the Fly"的繪者Summer McClinton畫哈維很貼近本人,對於需要仔細描繪長相的角色McClinton處理得不錯,而後面背景以及被簡化的旁人卻也能引起我的注意,對於區分甚麼是主要甚麼是次要McClinton表達的十分直接,有如攝影對焦後面的簡略粗糙部分。我甚至把所有背景及不相關的角色處理重新單獨挑出來看過,的確又是重溫國中選修英文那種簡單線條的風格,只是選修課本裡的人物連主角都是簡化的,這種畫風也讓我想起60年代披頭四”Yellow Submarine”的動畫風格以及德國導演Helmut Herbst的實驗動畫”The Cathedral of New Emotions“(Die Kathedrale der neuen Gefühle),雖然線條簡單,但寫實程度極高。
談論哈維可能一份碩士論文都不夠,若對他的文筆或是奇妙的談吐有興趣,也可以讀讀他的書評或是爵士樂評;他參與過電視節目精彩的如早期的The David Lettermen Show (哈維與主持人曾鬧翻)及波登不設限No Reservation中介紹克里夫蘭那一集 (哈維儼然已成為克里夫蘭的代言人,這集也有邀請漫畫家參與製作),帶著一種小人物對現實的諷刺,哈維即使在電視、電影上也都是以相同的態度;一生為了錢與工作苦惱,但成就不是吃好穿好、過奢華日子、有著響亮頭銜,而是對自己內心想創作的渴望誠實、對自己的感覺誠實,不過虛假、複製的人生。
Harvey Pekar on The David Lettermen Show :
哈維雖然不會被看作是偉人,但他的情感、思考以及創作都早已達到一種藝術的高度,即使強勢媒體不認識他、美國總統不認識他,我認識他、許多讀者認識他,將他的聲音當作自己的好友,描述著我們好奇的故事,創作者的份量在讀者心裡早已超越偉人、鉅富。因為作品跟自己共鳴、找到知音,這一種貼近的關係、接受者與藝術的關係,每讀一本作品都成為與讀者最個人、最私密的對話,哈維派克的作品便是這樣打動了我。
 |
| Harvey Pekar & Joseph Remnant |